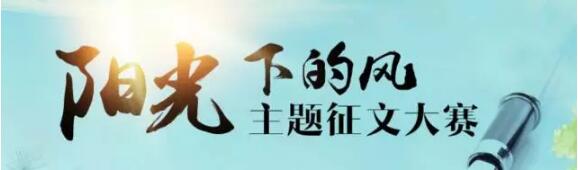
去年,由山东文艺出版社、大众网、《山东文学》联合主办的“阳光下的风”主题征文(原创作品)大赛正式启动。大赛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,网友投稿踊跃,参与热情高涨。
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学者最终选出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一等奖共4名,二等奖12名,三等奖25名;微电影一等奖1名,二等奖1名,合计43名。
我们将撷取其中优秀作品进行选登,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获得散文二等奖的作品,李继峰的《故乡的麦子》。
故乡的麦子
◎李继峰
想写麦子很久了,一直不敢动笔。麦子,作为天才诗人海子最重要的诗歌意象,已经蓬勃滋长在国人心田。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麦子,承载着农民丰收的希望,曾是幸福美好生活的象征。于我而言,麦子就像一位亲人,无论贫穷与富有,无论过去与现在,默默传递着营养与力量;它的味道像家乡阳光,一直那么温暖、温情。即便久居城市,到郊区游玩、回老家或出发,每年都能见到大块的麦田,总觉得麦田的颜色比童年要深,麦子却没有过去那么高大,便也少了麦浪起伏的壮观与诗意。问了专家,说现在都是低矮品种,能抗倒伏。
播种几天后的麦子,以极其柔弱的面目出在农人的目光里。深秋,鲁西南的田野一片萧瑟,麦地里却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用时髦的话说,麦子是“逆生长”的典型代表——天气越来越冷,麦子却成垄成行,生机勃勃。麦苗是幼小的,但绝不脆弱。它可以承受小伙伴们在麦地里欢快的奔跑和玩耍,即便猪拱羊啃,依旧茁壮。麦苗冬日蛰伏如竹,拔节如竹,空心亦如竹。它不畏严寒,以积雪为被,蓄积力量,逢春生长。禾苗干干净净,少有虫害。惟麦根细密,一如人类毛发。乡人笑话城里人不分麦苗与韭菜,我则觉得麦苗为满腹诗书之雅士,韭菜如脑满肠肥之富商,岂可同日而语。初中、高中学校的墙外即是大片麦田,早晨或傍晚,拿着课本,坐在田埂,背单词,背课文,背历史,曾是一景。曾听一成绩一般的同学,在地里背数学题——从开始背“已知”、“求证”,背到解答方法。当时对其学习方法很是不解,惊为天人。深秋的麦田,土松软如面,几乎陷进半只脚,田垄上的荠菜、米米蒿也嫩绿可人。边背课文,边拔一棵荠菜在指尖揉搓,荠菜的香气随着知识浸进鼻孔,浸进了脑海。米米蒿则断断不行,那股刺鼻的味道断然没有乡间的浪漫与诗意。学累的我们,在地里撒撒欢,跑一阵,吼几声。刻苦学习为了什么?自己既清楚又模糊,清楚的是,要考上学,摆脱这片庄稼地;模糊的是,考上学以后干什么?当过汶上一中校长的大舅常用这样的话教育我们:“庄稼孙,庄稼孙,庄稼人比别人矮三辈!”当了多半辈子右派,经历了从校长到农民的巨大人生落差,让大舅对农民的身份极其抵触、排斥。
麦苗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。麦粒,从正面看,极像人类生育器官,这也许是其生命力强大的一种原因吧。其时,很多家的猪羊是散养的,在寒冬里,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麦苗了。生产队的时候,村里组织麦田看护队,专门守护村边的麦田。猪羊们也像游击队员一样,神出鬼没,啃一口就跑。各家猪的特征都很明显,特别是老母猪,带着十多个猪秧子,极好辨认。认真的看护队员就找上门去,同主人理论一番。分田到户后,大家都注意了很多,除非猪羊自己从圈里窜出来。自己也干过类似的坏事。大哥买了一对家兔,家里的萝卜、白菜人都不够吃,哪舍得喂兔子。然后,就想到了麦苗。尤其是哪天电影散了场,就假装到麦地里解手,蹲在地里薅麦苗。当时没有什么塑料袋,麦苗就直接塞进怀里,冷嗖嗖的。兔子们很争气,长得也快,还生了两窝小兔。那么问题就来了,不知什么原因,兔子得了一种烂蹄甲的病,抹上洋油也治不好,死的死,卖的卖,很是伤心了一阵子。
春天的麦田是绝对不能踏进一步的。麦苗已经分蘖、拔节,一旦秸秆折断受损,就会颗粒无收。1986年夏天,到汶上县城考高中,在考场里就听到外面雷雨大作,出了场才知道,还下了冰雹。回家的路上,看到田野里成片成片倒伏的麦子,像一位受伤的无助的母亲,让人心疼不已。野庄西边的邻村叫河里,出过一起命案,一具无名男尸被捆绑着扔进我们常摸鱼捞虾的河道里。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县的大事,公安局去人就地解剖,周围几个村里的人全去观看。解剖过程很瘆人,传的很邪乎,眼睛、内脏都取走了,说警察局的机器能将眼睛里最后见到的人影取出来,从而找到凶手。尸身的其余部分解剖后就地掩埋在小路与河堤的交界处。那地方,是我家责任田干活、割草必经之地。那几年,交界处的一小片麦子长得分外高,分外黑,分外茂盛,每次经过,心就扑腾扑腾直跳,觉得那些麦子就像一个个站立着的人,让人头皮发麻,从来不敢停留。
割麦子充满了庄重的仪式感。麦收是仅次于过年的盛大节日,全村男女老少都在麦田里,大人收割,小孩拾麦穗,麦田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生产队要提前开会安排收割地块的顺序。大麦熟的早,小麦熟的晚;盐碱地、黑土地成熟早;黄土地黄的晚,最后收尾。割麦子的劳力数,赶车、装车、卸车的人数,还有做饭、炒菜、送水、送饭的,有时两三块地同时割,更要安排妥当。安全的问题更是绝对不能放松,麦子怕火,一洼麦子一个火星就能全部引燃,这也是有过教训的。即便麦垛之间也要留有适当的距离。抽烟的男人们要憋上一阵子了。农人们一年的希望和牲口们冬春的口粮麦秸都全靠这些麦子、麦秸。割麦子是令人疲乏、劳累而又充满技术含量的活。猫着腰,轮圆胳膊,镰刀在阳光下划过一道光,一束束麦子便应声躺倒,一只脚配合镰刀的推动,将割下的麦子移向前方,等一捆差不多大了,便单膝跪倒在麦捆上,将镰刀扎进麦捆的屁股,然后抽出一小束麦秆,将麦穗朝下就像码书一样理整齐,再然后将手中的麦束一分为二,麦穗对麦穗很快地搭接拧一个圈,乡人们将这个称之为麦葽。这时候便将麦葽放在旁边,一手抄起零散的麦捆一手用镰刀挑起放在麦葽上,再次单膝跪地两手分别抓住麦葽互相一拧,于是零散的麦子便成了一捆整体,一个麦个子就出来了。人不可貌相,一些五大三粗的汉子割起麦子有时还不如瘦小的妇女。一人三五垄,地头上找齐。队长则在后面督查、提醒,谁的麦札高了,谁的丢穗多,毫不客气。装车的小伙子要选最能干、最有力气的,用铁叉挑起一个个麦个子,喊着号子往车上扔,装车的人则分层仔细码放。哪个生产队运送麦子的马车在半路塌了垛,那是被其他生产队要嘲笑好几天的大事。白天割麦,晚上是不能休息的,老天不等人,要趁着天气好,赶紧打出来,这样才好晾晒。一旦赶上连阴天,麦垛焐了,全队都要吃焐麦子,那还得了啊。打麦机噪音极大,往里续麦子也很危险,邻村就有把人的胳膊绞进去的。这也是收麦子过程中最脏、最苦的活。机器轰鸣,粉尘飞扬,整个场上的人衣服都湿得透透的,头发打了绺,抠一抠鼻孔,全是黑泥。有些麦子则摊在场里,为了能晒透,需要到场里没膝深的麦秸里不停翻。等到干透了,牵着牛马驴骡,拉着碌碡,转圈碾压。最后的麦秸要集中垛几个大垛,喂养生产队的牲口。
分了责任田,各家各户割麦子也多多少少地保留了生产队的模式和程序。爷爷、父亲提前几天磨好镰,准备好草葽子,给地排车打好气,一早一晚都到地里转转,看看天气、墒情和麦子的颜色,奶奶、母亲则忙着收拾腌肉的泵子里长了绿毛的方子肉和咸鸡蛋、咸鸭蛋,还要擀单饼、蒸馍馍。开镰的那天中午,奶奶不顾小脚行动不便,提着开水、白饼、咸鸭蛋、咸肉,亲自送到田间地头。我曾多次参与家里的麦子收割,爷爷、父亲割五垄,我割两垄,还老是赶不上趟,麦札也忽高忽低。以前的麦子多是长芒,一个上午下来,我手脖子上扎得全是血点子,一出汗,疼痛难忍。中午,树荫下的奶奶常念叨,家里原来有十五顷地,割麦子要请很多帮工,帮工们都是吃最好的,肉不够吃哪行啊。我知道,奶奶心中有一个心结一直没有打开。文革中,把所有的地主、富农都刻画成刘文彩,别人家情况我不知道,起码我家远非如此。一队的杨姓长工同我家保持了一生的友谊,即便文革期间,也常常趁夜深人静偷偷到家里探望爷爷。1989年5月,在爷爷的葬礼上,他痛哭流涕,如失亲人。在这里,我没有翻案的意思。时代发展和评价标准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。如今,马云等社会精英,要按昔日标尺,也是万恶资本家,剩余价值的理论也适用于他,只不过世事变迁已今非昔比。
经历秋凉,冬寒,春暖,夏热,由一粒麦子回到一粒麦子,跨越四个季节,三百多个日日夜夜。麦田里几无杂草,偶尔有一棵芙苗秧爬上枝头开着粉红的喇叭花,与一片金黄的田野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割麦子的过程也有很多惊喜。突然会窜出一只野兔,在一片惊呼声中有人扔下手中的镰刀追上去,也有家里的土狗上前追逐。只有那些叫细狗的家犬捉得住成年野兔。小兔子几乎每年都能捉上两只,布满黑点的不知名的鸟蛋也是常见之物。小野兔很难养,弄回家去,不吃不喝,一两天就死掉了。放在炕上包在棉絮里的鸟蛋也从来没有孵出过,但我们几乎年年重复这样的过程,乐此不疲。一串串已经变黄的马匏也让我们不胜惊喜。找一些没有完全成熟的青穗,揪上两穗,放在手心两手狠搓几下,吹去麦壳,绿绿的、胖嘟嘟的麦粒就躺在了掌心,捂到嘴里一嚼,甜丝丝,很筋道。也有人掐一些青穗拿回家,在锅底燎一燎,也叫烧麦子,搓一搓,又香又甜。运完麦子的麦田才会让人捡拾,叫放圈。有的麦地割得毛躁,横七竖八丢穗多。小学时,学校组织捡麦穗,拾了三天,最后分了一毛七,同班女生李爱珍很是能干,分了八毛九,让人羡慕极了。初中一年暑假,跟着父亲去南站镇粮所卖麦子,粮所的一个一脸横肉的人很粗鲁,拿个粗粗的尖锥子直接捅装麦子的口袋,一捅一个窟窿,麦子也洒一地,父亲心痛得直咧嘴,还要陪着笑脸,请人家评个好等级。
生产队一年一人300斤多斤的口粮,包括瓜干、玉米、小米、高粱,麦子最多几十斤。劳力少、孩子多的人家自然是不够吃的,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,父亲就满街借粮食。麦子,给我童年带来最美好的记忆与享受。肉、油、麦子,是最美好的三种食物,却只有麦子,久吃不厌,吃多不伤。麦香,是其他食材难以带来的素淡之香,熨帖着味觉与身体。装病装秧,想喝面汤。小麦用最好的瓷缸存放,麦面的面缸要放在奶奶屋里。老人、孩子头疼脑热,母亲就挖半碗白面,揉成一个面季子,与玉米面窝窝一起蒸。掀开蒸笼的刹那间,就能闻到麦子独特的一缕香味。待水雾散去,那个馍馍在一锅黄色玉米窝窝的环绕下,那么耀眼,那么卓尔不群。
即使再穷的人家,过年蒸干粮也要蒸两锅白面馍馍。因为年后要待客,白面馍馍是必备之物。走亲戚都知道要留一点饭量,各家都不宽裕(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),吃上一个馒头,就说饱了,主人再推让也不吃了。菜也是如此,都吃光了显得主人待客不周全,也都知道,几个嘴馋的孩子还在厨屋里眼巴巴地等着。饭后送客,亲戚刚出大门,这边看谁跑得快,一个逮一个盘子,风卷残云,舔得干干净净,省得刷了。那时常讲一个外甥走姥娘家的故事。姥娘家上了一个粉皮炖白菜,粉皮是很厚的那种,铺在盘底,白菜在上面。懂事的人只会叨菜,粉皮明天还要待客。外甥不知道这个,看着都不吃粉皮,端过来盘子就扒拉着吃了。妗子那个心疼啊,又不好说别的。说来世界万事万物真是奇怪,地瓜干是白的,高粱也是白的,熟了就黑乎乎的,小麦则越熟越白。地瓜窝窝板结如土,味同爵蜡;玉米窝窝干涩粗糙,握之即碎,入口难咽;馍馍则温和暄软,入口即化。都是一样的粮食,差距怎么这么大呢!
父亲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,冬天,麦秸是牲口的主要饲料,那些大牲口(马驴骡)偶尔加一些从微山湖拉来的湖草。白天,用切刀一截截从麦秸垛上切下来,然后用铡刀铡成两厘米多的小段。麦秸经过碾轧,叶子早已脱落,只剩主干,非常洁净。铡好的麦秸堆放在一大间敞门的屋子,常偷偷钻进去,躺一会,爽滑温暖。这些麦秸在送到牲口槽子前,还要放到捞草缸(一敞口大水缸)里淘一淘。水缸里的水夏天三天、冬天五天一换,倒了水,缸底会有20度多厘米的淤泥,淤泥里还有让人惊喜的宝贝:麦粒!每次换缸,就会有三斤多麦子的收获,这是麦秸里夹杂的麦子。三个饲养员轮流享受这种密不外传的福利。缸里捞草水,因为泡过很多麦秸和麦壳,水的颜色与酱油无疑,酸酸的气味却与酱油全然不同。当时有一个偏方,谁家孩子脸上青春痘起得厉害,舀一茶缸子捞草水,回家抹脸,效果明显。我家大哥近水楼台,去牛屋就抹抹,也不知有没有用。
麦子的高产得益于良种推广和化肥普及。1985年以后,乡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上白面,这代表了乡人食物结构的根本改变。当然,后来肉食的普及又是一个飞跃。那些长芒麦子已全被短芒葫芦头麦子替代。在麦子刚刚普及的那几年,各村都有一个磨面坊,磨面机后面拖着一个长长的袋子,印象很深刻,那可是村里的重工业项目。见过卸开修理的磨面机,很是复杂,后来一些讲究的人家开始吃出麸子的85面。
近些年,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,老家大量的麦田被种上了果树或树苗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,种麦子的人也越来越少,打麦场的麦垛子便成了稀罕之物。那些不肯罢休的老年人便在麦场的周边开垦点土地种上了大葱小蒜,那些当年麦田里猫腰挥舞镰刀的热闹场景已是不可挽回的过往。联合收割机也早开到了家乡,乡人们不再受割麦、打场之苦累,轰隆隆,哗啦啦,干净的小麦粒直接就出来了。外出的时候,也见很多地方更是省事,直接在柏油路摊晒麦子。麦子,在农人的眼里,变得越来越平常,与其他作物已全然无异。
去年,在转山西路的山师新村小区花坛,曾见一丛麦子迎风摇曳,我就像见到久违的亲人。乡人,就像麦子,一茬一茬,在村庄上生老病死,繁衍存续,平凡普通。他们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,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,在这套价值标准的指引下生长死亡。在城市化大潮中,乡人们打工,求学,奔亲,工作,娶妻嫁人。特别是女孩,很多远离家乡,生儿育女,就像一颗颗被运往他乡撒播的麦子,在异乡甚至是异国落地生根。野庄的村人已经有100多家在县城安居,只是偶尔回村收拾一下老院,给树木、花草浇浇水。这些年,在济南,我遇到、结识了很多乡人,甚至是村人,有的是朋友的朋友,有的是工作中无意遇到聊起,有的通过博客、QQ、微信相识,借助互联网与手机,我们这些甚至从未谋面的人有了特殊的亲近与信任。我这一口标准的“汶普”也使得我像一辆汶上的流动宣传车,让听到声音的人好奇、搭讪。就像诗里说的:一切都似曾相识,甚至擦肩而过的问候,也充满情谊,每一张笑靥都充满亲缘。
这是一个漂泊的时代。时代像一条奔腾的河流,挟裹着我们前行。自己何尝不是一直在路上在流离、奔波,县城,聊城,泉城,城越来越大,家越来越远。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!为了明晰或者模糊的理想,我们都在追寻一种别样的生活。异乡的挣扎与拼搏,孤苦与寂寞,更与何人说!返乡一杯酒,淡看苦与累。一年过年,与亲戚们在家里吃饭喝酒,一亲戚恭维我,说我家祖坟上冒青烟了,出了这么大的官。好在自己清醒,我就一普通干部而已,真是哭笑不得,也想逗逗他,说你这话不假,很多人见过我李家祖坟上的青烟。这回轮到他张大了嘴。我告诉他,我家祖坟南侧,有一条三百多米长、三米多深的排水壕沟,近些年很多人把玉米、棉花、小麦等作物秸秆就堆在里面。冬天赶集路过的人,个别使坏,故意丢个烟头,常会引燃秸秆。由于秸秆半干半湿,常要烧上十多天,且只冒烟不冒火,这不是青烟是什么啊?!听完我一席话,亲戚的泪都笑出来了。如今,亲友们偶尔在饭店聚餐,最后上面食,我都提议吃清水煮面条,几乎每次都能得到他们的赞同。我知道,在每个人心里,都保留着小时候母亲端过来的那碗香香的不放任何佐料的清水面条,那才是麦子的味道,那才是世界上最美、最幸福的味道。
